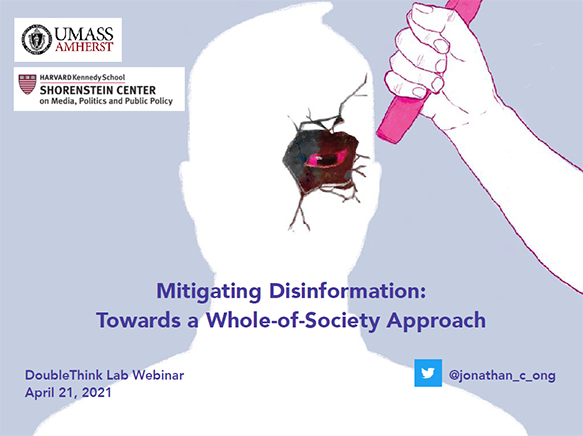本文是Jonathan Corpus Ong博士於「公民社會對抗惡意不實訊息能力建構網路研討會」的演講逐字稿。
許多參加今天這場網路研討會的與會者,一直以來皆處於艱困的資訊環境中。在這樣的環境裡,仇恨言論、騷擾、抹紅攻擊等,不僅已成常態且日益加劇。在過去幾年裡,我們看到一些政客策略性地散播意圖製造及加劇政治分歧的敘事;這種行為不僅未受到懲罰或譴責,反而為他們吸引更多民粹派的選民、可靠的死忠鐵粉。另外,對惡意不實訊息活動的策劃者來說,散播「假新聞」還可帶來額外收入,創造地下(影子)經濟。對於這一點,他們甚至不加以,或懶得掩飾。由於惡意不實訊息活動往往可帶來新案子和新客戶,許多人更是樂於將對其之散播歸功於己。
學術界、新聞界、法律界、社群組織,以及第一線公民運動團體在各個領域皆發起了各種不同的倡議和活動。我很想知道在座各位的看法,相較於四年前「假新聞」和「酸民大軍」的詞彙首次在全球出現時,我們目前的景況是更好還是更糟?
一方面,我們在調查性報導、學術研究與公民社會能力之建構皆得到更多的資金和策略性投資,這些都帶來了新的工作機會、新聞報導路線和研究領域,以及「反假新聞」法案和更為激進的「平台驅逐」行動,例如,將唐納‧川普和他的忠實擁護者陰謀論團體「匿名者 Q」(QAnon)從平台驅逐。
而另一方面,破除惡意不實訊息與事實查核的任務又十分艱巨,就如同要將九頭蛇的頭全部砍掉一樣,當一個頭被砍掉時,同一處又長出更多的頭。另外,在文化與實際現況上也有挑戰:一個地區或文化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能無法適用於另一個地區或文化;舉例來說,在矽谷發展出來的文化規範能有多大程度的適用於其他國家或文化的脈絡裡?那麼,我們能如何賦予地方層級科技監管的權力,使其能在選舉法和稅法上進行改革,以及給予記者和公民社會應有的保護?
這場網路研討會的目的是邀請大家共同合作,發展涵蓋全社會的方法來對抗惡意不實訊息。
以全社會方法對抗惡意不實訊息的重要原則為:
- 多方利益相關者原則
這個原則指的是拒絕孤軍奮戰,並以非競爭的方式合作,藉由多元的社會背景與不同的學科專長來預測惡意不實訊息的新趨勢,以及一些善意的干預措施可能會產生哪些非預期的結果。 - 結構性原則
這個原則指的是從根源處理惡意不實訊息的製造,而不是採取糾正性、修復性或標籤化的措施。這需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檢視惡意不實訊息,它的運作方式與人員配備,以及其作為一個看似正當的產業,與數位地下經濟共謀和勾結的情況。 - 在地性原則
這個原則指的是對那些有針對性的惡意不實訊息、仇恨言論和陰謀論要有更高的敏銳度,特別是其對少數族群、婦女、LGBTQ+ 族群、移民和難民所造成的社會傷害。這個原則也需要賦能予在第一線對抗惡意不實訊息的工作人員,讓他們有能力保護自己。
今天的網路研討會,我將用一些我之前做過的研究來作為討論的依據。
這些研究包括一項2018年的研究〈惡意不實訊息網絡中的製造者〉,該研究在菲律賓2016年大選期間採訪了選舉策略師及其徵召的政治酸民,並將採訪結果製作成分析報告。
2019 年的報告〈追蹤數位惡意不實訊息〉聚焦於 2019 年的選舉,記錄了從超級網紅轉移到微網紅和封閉社群的現象。
2020 年的研究以比較法視角和跨區域方法來研究東南亞的選舉,研究問題為,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大選敘事及其製造者的共同之處,以及選舉和社群媒體新法中,我們能學到什麼?
我最新的研究(2021 年)聚焦於菲律賓的人權工作者,以及在過去四年間,當人權工作者面對來自國家行為者以及網路酸民的各種攻擊和陰謀論戰時,人權組織在策略性傳播上是否有進行投資,或缺乏投資。研究問題是:「人權組織在多大程度上賦能予組織團隊中的傳播人員和數位工作者,使他們有能力打擊假新聞?」此報告是哈佛大學一項大型研究計劃「惡意不實訊息的真實成本」下的一部分,在此計劃中,我們不僅研究惡意不實訊息帶給各個組織的財務成本,也研究那些參與惡意不實訊息工作的相關人員的人力成本與情緒勞務。
我今天將為大家概述一些相關的研究發現。
一個降低惡意不實敘事影響的重要方法,是靠多方利益相關者進行合作,並找出可有效對抗的報導或進行研究。以研究人員和新聞記者來說,可在 「策略性沉默」 及緩和激化的議題上進行合作。策略性沉默指的是,編輯部為預防某些族群遭到針對性暴力之行為,而決定儘量減少報導某些極端想法或意識形態。
僅致力於事實查核的一個根本問題是,這麼做可能更加提高社群媒體影響者之知名度,使他們的極端想法更為普及,包括 COVID-19 陰謀論以及針對種族的惡意不實訊息。
我們應該找方法讓資助者也能參與進來,讓事實查核倡議的廣度能夠增加,以及提供創造性的合作空間,促進事實查核者、記者和學者間進行批判性的對話與相互檢視。我們應該尋求能夠直接合作的方法,而不是在各自的孤島上努力,目前這種孤軍奮鬥的做法已被證明效果不佳。
一個地區的研究人員可更積極地提醒當地記者採用「策略性沉默」,對於極端主義想法和仇恨言論不予報導。另外,鼓勵和促進學術界與記者進行批判性的合作,在如何報導危機事件上可形成指導,並減少仇恨言論。
在報導疫苗接種的猶豫現象時,我們需更為謹慎。
在報導或點名惡意不實訊息活動幕後的影響者或操盤手時,我們需更為警覺,因為這樣的報導有可能使他們獲得更多的關注、宣傳和客戶!
在思考如何揭露亞洲地區惡意不實訊息的地下經濟時,結構性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在美國,各個極右翼團體基於自身的意識形態,致力發展仇外以及/或仇視女性之敘事,並在網路上散播這些言論來達到政黨的目的。然而,在許多亞洲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許多製造惡意不實訊息的作者其動機並非出於自身的意識形態,而是出於經濟原因。這就需要運用稅務和調查等工具、行業自律委員會和媒體監督來了解惡意不實訊息這個產業。我們還需要進行更多的調查,以了解此產業中各個實務領域,如搜尋引擎最佳化、駭客、數據分析公司、迷因粉專經營者和網紅代理等,他們所需負的責任以及/或之間的共謀關係。
賦能予地區研究人員也有助於分散對矽谷「科技大佬」的廣泛關注,並推動應如何對 LINE 和 Viber 等擁有高人氣的亞洲通訊平台進行監管的相關討論。此外,促進散居在美國的南亞和東南亞研究人員與當地研究人員和公民社會建立跨國社群關係,也有助於統整各規模層級的問責倡議,在這裡也可探討或分析自上而下的立法框架是否能符合當地的文化和規範。
「政治-利潤」運作模式的討論
我們需要檢視惡意不實訊息對社會的危害,以及它與仇恨言論和陰謀論之間的模糊界限,並了解它對負責降低「假新聞」衝擊的一線工作人員有哪些影響。
COVID-19 疫情爆發之後,反華和種族歧視言論以及陰謀論在全球各地興起,遺憾的是,東南亞國家也受到波及。對於這些仇恨言論,一些記者未能進行事實查核,也未試圖找出其傳播者,反倒是在個人網頁上轉發這些仇恨言論,或在全國性報紙上轉載這些陰謀論。
有時,網路上的言論倒向針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言論,這對多元文化的社會關係構成了威脅。
遺憾的是,一些亞洲新聞媒體記者只是更加堅定其立場,不對這類惡意不實敘事進行事實查核,有些記者聲稱這是一種「虛假對等」,或「仇恨言論不是惡意不實訊息」。
仇恨言論可能導致暴力,與惡意不實訊息的界限也相當模糊。關於亞洲國家的仇恨言論和種族主義,在地記者、公民運動人士和學者需要制定長期的研究目標,此目標需與亞洲歷史及社會脈絡裡特定的種族階級和權力關係有關。在亞洲國家,我們在種族問題上,及其與階級、性別、性取向的關係上存有自身的盲點,因此,確保新聞編輯部、公民社會和學術界的反種族主義會是項重要的投入。
我們也必須抵制資助者在國家安全議題上的操作,將「外國干涉」定調為俄羅斯或中國的問題,因為這樣的操作往往不是為了處理當地的議題,而是為了達到地緣政治目的的一種策略。
組織可從內部做些什麼來建構能力?
組織可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投資那些實際面對惡意不實訊息並做出回應的傳播工作人員。
從我們對菲律賓人權組織進行的調查發現,人權提倡者認識到,對於飽受「假新聞」以及反建制敘事轟炸的公眾來說,認識人權與重建其重要性具有重大的意義。然而,在認識到這一點之後,卻幾乎沒有任何直接投入於支持此類建設的物質或人力資源。
人權人士持續將傳播視為一套互不相關的工具、活動或平台,而不將其視為可用來奪回政治敘事控制權的長期且連貫策略之一環,或是可用來重塑公眾對人權的參與和看法之工具。 雖然大多數組織在面對公眾的溝通時能做出即時的「調整」,但卻缺乏對技能與人員的重視以及實質投資,進而導致表面上的、無持續效益的努力,並弱化了組織有效解決危機的能力。
傳播和技術工作者在人權組織中持續扮演著邊緣的角色,很少參與整體的策略規劃。 在我們採訪的組織中,幾乎有一半(46%)的組織沒有專門負責傳播或品牌建設/推廣的工作人員;一些組織只在有計劃/活動時配置短期的傳播人員;而其他的組織則僅使用無償的實習生或志工來做傳播的工作。
組織在決定要以公開還是暗地裡的方式挑戰民粹主義領導人時,需具策略性,並可根據計劃的目標在特定的時刻進行調整。當盟友受到攻擊時,組織也應提供支援。
現在就以下面這些問題來結束討論:
- 如何讓支持民主的聯盟更加多元化,以及更具包容性?
- 學者和記者能如何合作?畢竟要與自己所屬新聞機構賴以為生的企業廣告金主對立,記者的意願可能不高。
- 外國捐助者能如何支持在地公民社會和研究人員,倡導「自下而上」地進行科技監管?